罗伯斯庇尔墓志铭(从法国大革命看罗伯斯庇尔)
说起罗伯斯庇尔,笔者便想到了流传在其身上的一个幽默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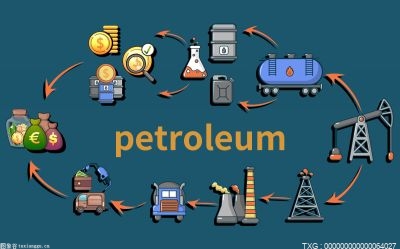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相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在上台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将成千上万人推向断头台,最著名的便是那个路易十六的国王,也不知是不是风水轮流转,在后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被抓捕,也同样被推向了断头台,在他的墓碑上,幽默的人们留下这么一段话作为墓志铭:
“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不要为我的死而哀伤,因为我要是活着,你们都活不了”
一提到罗伯斯庇尔就说是独裁者,狂热主义分子,这样片面化的认知,事实上是很不利于我们解读这个人物的。
仔细审视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涯,无论是他在民众中的演说还是在议会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养,绝对不像人们口中说的那样激进或狂热,与之相反的是,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是极为理性的,并且是极度克制自我的理性。
在他还没有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共和党人之前,他便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否决条款”,即规定“所有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后四年内不得担任公职”,给了他所认为的对民主的一个保障。同样,罗伯斯庇尔从来不像是独裁者,他曾对他家门口的请愿者说:“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他所维护的是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
我所说的并不是为罗伯斯庇尔后面的恐怖统治洗白,在他当权期间,将成千上万人送上断头台无疑是赤裸裸的恐怖统治。
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应该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言人,他天然对民众的力量感到恐惧,然而矛盾却在于他认为革命成果的巩固必须依靠巴黎人民,所以他必须与其周旋。而作为应对和消解民众给他们带来不安的方式,他曾经反复强调以美德教化人民,但是在大革命很短的时间内,道德对社会的推动只能是收效甚微,最后他只能不可避免地滑向了高压恐怖统治。
学者威廉多伊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曾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问题在于,他从未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这导致了政治生活的混乱。可实际上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像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例如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
在当时,他们将党派视为一种侮辱。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与英国的封建主所享有的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路易十四更是自称太阳王,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的权柄。
因此在法国的体制内,从未出现过大宪章这样贵族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更不提英国那样的议会传统,即使是和英国议会大相径庭的三级代表会议,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也有一百多年没有召开了——我们可以说,以三级会议作为代议制方案,正体现了法国议会制传统的匮乏。
与此同时,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话语权空间,即民间自发的政治团体。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不定期的举行论战,形成一套自己的公共舆论,到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制的后期,随着君主权威的逐渐下降,公共舆论逐渐成为政府政策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基石,甚至于国王也不得不忌惮公共舆论几分。
精英们在民间社交团体中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进行自己的政治构想,君主立宪派和民主共和派争吵不休,但共同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将被重塑,人与人之间将真诚而透明。
与英国议会中一般是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实施与否的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在共同的价值诉求上,人们关注大的政治结构的确立,从来不会因为现实来徐图改良,人们尽力马上就建立起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框架。所以,如果说英国的革命不得不妥协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在旧瓶子里装新酒,那么法国的革命则是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在真诚而透明的社会关系上重建一个启蒙价值主导的全新共同体。
基于这样的理念,革命者认为普遍的真诚与美德是可以实现的,而政党只会因为各自的所代表的私人利益分裂这个共同体,所以罗伯斯庇尔们是具有伟大理想主义情怀的,他们坚信,启蒙思想中的普世价值一定是未来共同体的磐石。
然而这里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于共同价值的追求加剧了人们对潜在政党的敌视,而为了在这种敌对中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抱团寻求庇护,并且不自觉地开始党同伐异,最终另一种事实上的政党形成了——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的指责,吉伦特派绝不会走到一起。
但是这种形势下造就的政党并不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再加上法国议会政党传统的缺失,失去了秩序与规则的政党冲突无法造就宪政,只会形成无穷无尽的混乱,所以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悖论在于:作为一个共和国,他天然的抵制作为共和国基础的政党政治。
除此之外,与封闭的议会辩论不同,为了获得支持者,政治团体的演说文化一定会开放化,也更为贴近民众,这也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权和影响是一个不断下移的过程。
随着革命的推进,人们在这种争辩性的思想熔炉中逐渐萌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了自己的革命诉求,传统的阁楼式贵族政治已经控制不住革命的局势,斐扬派的急速失势很大程度上就与俱乐部文化有关,相信君主立宪和精英政治的他们,在1791年仍然选择私人聚会而非公开演说,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加入雅各宾俱乐部,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宣传形式,他们都无情的被公众淘汰了。
然而公众宽泛的民主引发的不可收拾的混乱最终引发了罗伯斯庇尔的担忧,罗伯斯庇尔为了遏制这种恐怖,开始倡导美德,在收效甚微之后,便选择用恐怖去制裁,最终他走向了疯狂,而他本人似乎也预见了自己的结局,在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前两个月的一次演讲中,罗伯斯庇尔激动神经质的说:
“我是法国人,是你们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清接受我本人这一祭品吧!诞生于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为你们的福祉而死会更加幸福!”
所以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本身便是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剧:一个公认的不可腐蚀者、一个在1791年提出自我否决的议员、一个可能是最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却最终创造了恐怖。
当然,罗伯斯庇尔的悲剧命运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这种政治文化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他创造了基于公众参与的共和传统,而这也是英国传统所缺失的,从此政治不仅属于国王、贵族甚至革命领袖,也属于公民。
1789年的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人们的政治觉悟开始启蒙,从此启蒙价值深入人心,国王的命令没有议会的承认就不能颁发,贵族对公共财物的侵占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不仅属于资产阶级,更属于全体公民,革命精英们走上街头,用他们的政治观点去获得民意的支持,在他们头上的,是永不下降的三色旗。
共和派信奉这些理想,并且忘死的去推行他们,不是仅仅是他们吸引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而更是因为他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继承了从古代希腊和罗马广泛的政治参与的民主理想,并且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方式给他们披上了一层新衣,那就是民主选举、广泛的责任心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一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思想胜利的光芒。
不由想到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这一根本真理。
我们可以预见,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将会随着大革命的进程,在欧洲掀起一场无与伦比的社会变革。

